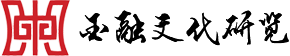金融文化参讯—陕西(赵晓舟)自恋,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,在生活中屡见不鲜。文学领域中的“自恋”,并非浅薄的自我陶醉,而是创作者与文字深度交融时所展现的一种锐利精神特质——它既是作品诞生的内在驱动力,也可能成为读者与作品间的无形隔阂。
此种“自恋”的首要表现,在于创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“自我审视”。作家执笔之际,本质上是在剖析自身的感知、记忆与思考,将高度私人化的情绪与认知熔铸为文字。此种对“自我认知”的笃定,构成了文学创作的起点——若非确信自身观察能触及普遍人性,便难以拥有将私人体验升华为公共文本的勇气。其第二层表现,则是对“文字纯粹性”近乎苛刻的坚守。诸多文学创作者有意识地疏离“流量逻辑”,拒绝为迎合市场而简化表达或稀释思想。他们痴迷于文字的韵律之美、意象之精准,甚至为一个词汇的选用而反复推敲数小时。此种严谨态度在外界看来或许形同“自视甚高”,实则是对文学审美底线的守护。恰如诗人于绝句间细琢平仄,小说家在叙事中巧埋伏笔,这种对“专业门槛”的坚守,赋予了文学区别于通俗娱乐的厚重质感,却也可能使作品趋于晦涩,在圈外人眼中沦为“自说自话”之境。
文学的“自恋”虽为常态,然而,过度的“自恋”亦会沦为陷阱。部分创作者将“私人化”误解为“排他性”,致使作品沦为仅自己能解的密码,忽视了文学作为“沟通桥梁”的本质;另有部分创作者沉溺于“圈子化”的自我陶醉,以标榜小众为荣、鄙夷大众为俗,最终使文学沦为封闭的小圈子游戏。真正成熟的文学创作,绝非孤芳自赏——它始于对自我的深刻剖析,终于对他人与世界的深情观照。正如鲁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尖锐背后,深藏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赤诚。这份“自恋”的底色,归根结底是对人性的深切关怀。
若对文学领域的“自恋”进行更为具体的剖析,可发现其不仅潜藏于文学创作的字里行间,更贯穿于文学传播与评价的全链条。它既曾催生出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,也暴露出文学圈子生态的潜在问题。
首先审视创作层面的“自恋”之具象——部分作家易陷入“经验闭环”之困。他们依赖有限的人生经历构筑写作版图,将个人记忆无限放大为“普世叙事”。例如,某些聚焦都市精英生活的作品,反复描摹咖啡馆、艺术展、职场博弈等精致日常,却疏于呈现更广阔的社会图景,仿佛认定其个人生活样本就是‘值得书写的全部’。此种“自恋”并非刻意傲慢,实则是创作视野的自我局限,犹如固守一方池塘写作,却将池塘错认为浩瀚海洋。
其次观察文学评价中的“圈子化自恋”。部分文学评论形成专属的“话语密码”,以堆砌理论术语代替真诚的文本解读——分析小说时,避开人物情感张力,仅论“叙事学中的视角越界”;品评诗歌时,不涉及意象所传递的情绪,只谈“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解构”。此种解读方式,看似彰显专业深度,实则是为圈子划定“准入门槛”:能解读此术语者方为“圈内人”,反之则被归为“不懂文学”。更有甚者,圈内互评陷入“互捧式默契”,对彼此作品瑕疵选择性无视,将“同行认可”置于“读者感受”之上,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评价闭环。
然则,“自恋”的另一面,亦承载着文学创作的珍贵坚守。汪曾祺书写高邮鸭蛋、沈从文描绘湘西沱江,皆从个人熟稔的故土与记忆出发,却因笔下蕴藏对生活本真的挚爱,终能引发跨越地域与时代的共鸣——其“自我凝视”始终锚定于“人性共通点”。这些拒绝迎合流量、坚持独立创作的作家,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主题和复杂的叙事结构。例如,余华在《活着》中以冷峻笔触书写苦难,这并非刻意追求“小众”,而是坚信文学应具备承载沉重思考的力量。此种对文学价值的坚守,恰如构筑起一道抵御娱乐化消解的坚实屏障。
真正的文学创作,需要适度的“自我信任”,却须警惕过度的“自我封闭”。它应如一扇窗,作家从自身视角将其推开,让读者不仅能窥见作家的内心世界,更能透过此窗,望见更为广阔的人生图景与世界万象。
以行业作家的创作为例,可观察文学领域中的“自恋”如何在“自我坚守”与“自我封闭”之间摇摆不定,从而更清晰地把握这一特质的边界所在。行业作家常在专业壁垒与大众共鸣之间寻求平衡,其创作既要依托职业经验的真实性,又容易陷入术语堆砌、视角窄化的困境。某些法律、医疗题材的小说,虽细节严谨,但通篇充斥着程式化对白与行业困境的单一呈现,忽视了人物深层心理与社会关联,仿佛只为赢得同行拍案叫绝而作。同样,金融题材写作亦难逃此律,专业术语的堆砌易使文本沦为行业内部的话语游戏,而真正动人的作品,如《追风者》《繁花》《城中之城》,皆能将资本流动的冷酷逻辑与个体命运的悲欢紧密交织,以具体人物的沉浮折射时代浪潮。它们不回避行业的专业属性,却更聚焦于人在欲望与规则间的挣扎,使叙事突破圈层壁垒,直抵普遍生存境遇。此类创作证明,行业经验不应是自我重复的牢笼,而应成为通向公共议题的桥梁——唯有当“自恋”转化为对他人生活的深切体察时,文学才真正履行了其见证与共鸣的使命。
近十余年来,诸多文学作品在技术加速与阅读碎片化的浪潮中重新锚定自身,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描摹,而是试图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构建更深的联结。那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,往往既扎根于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,又敢于走出私域的舒适区,以虚构之力填补真实之隙,让边缘的声音被听见,让隐匿的情感被照亮。它们不回避写作的主观性,却始终怀有对世界的好奇与谦卑——正因深知“我”之局限,才更需倾听“他者”的声音。这种由自恋转化而来的共情姿态,使文学得以在自我与社会、特殊与普遍之间持续摆渡,成为一面既能照见自己,也能映出众生的明镜。
审视部分名人名作的文学立场,诸如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,不仅是对个体精神胜利法的嘲讽,更是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剖析;张爱玲笔下那些被困于婚姻与欲望中的男女,不仅是海派都市的浮世绘,更揭示了人性在压抑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困境。他们的写作虽带有个人视角的印记,却始终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。这种以自我为起点、最终超越自我的叙事路径,正是文学“自恋”得以升华的关键所在——它并不否认作家的经验根源,但更强调以此为契机,深入他者的命运。其拒绝将文学简单等同于“故事消费品”,坚持以厚重的叙事探讨时代与人性的复杂,即便作品因此不受大众市场欢迎——此种对“文学严肃性”的坚守,是对抗流量化浪潮的“清醒自恋”,守护了文学的精神内核。然而,其偶尔在公开表达中流露出的“小众优越感”,将“大众接受度”与“文学深度”对立起来,认为不被理解的作品更具价值,这又陷入了“圈子化自恋”的误区:文学绝非“小众”的专属标识,真正有力量的作品,既能保持思想的高度,也能让普通读者感受到其温度。
在文学产业化的当下,文学的“自恋”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挑战。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出版行业的商业化运作,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。一些创作者为逐利,看似挣脱了传统的“自我禁锢”,却陷入了另一种“自恋”——对市场与流量的盲目趋附。他们依循热门题材与读者偏好批量创作,作品内容千人一面,欠缺深度与个性,宛若只是在复刻市场上已然成功的范式,将文学创作异化为一种机械的生产行为。这种对市场的过度倚赖,实则是一种对商业成功的“自恋”,他们仅关注作品能否带来经济收益,却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。
与此同时,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,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发展也加剧了“自恋”现象。作者们借由各种渠道宣扬自己的作品,与读者互动,构筑了一个个以作者为核心的小圈子。在这些圈子里,作者往往仅聆听粉丝的赞誉与支持,对异见之声则选择性漠视,进一步加固了自我认同。读者也在这种氛围中被划分成不同的群体,形成了各自的“文学部落”,只阅读和讨论自己喜欢的作者的作品,排斥其他类型的文学。这种文学传播的碎片化和圈子化,使得文学交流变得更加封闭,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。
然而,文学的发展也并非完全被“自恋”所束缚。一批新兴文学创作者正试图突破既有格局,他们巧妙融合新媒体特性,以更为开放与多元的姿态投身创作。譬如,部分网络作家借助与读者的即时互动,依据反馈灵活调整故事脉络,既满足了读者的参与欲望,又防止了作品陷入狭隘的创作窠臼。与此同时,诸多文学奖项与活动亦积极致力于文学的普及与交流,激励创作者聚焦社会现实,跨越文学圈层的壁垒,使文学作品真正融入大众生活。
编辑:本站
审核:叶子
点赞: +1 16次